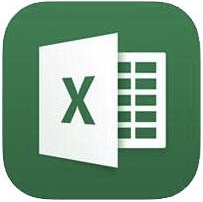馬亮:“地攤經濟”考驗城市治理的平衡術
?新聞 ????|???? ?2020-06-05 15:01
文 | 馬亮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治理學院教授)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東麗區華明街胡張莊村股份經濟合作社黨支部書記、理事長楊寶玲提出的“地攤經濟”建議,引起了人們的普遍共叫。她以為城市治理既要規范,也應因地制宜。地攤經濟是宜疏不宜堵的典型領域,因此“不能光圖省事‘一禁了之’”。城市政府要探索和創新城市治理模式,真正開釋地攤經濟的最大活力。
“兩會”期間人大代表重提地攤經濟,讓這個塵封多年的老大難題目再度熱起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在接受搜狐智庫的采訪時指出,地攤經濟既能夠增加就業,又可以便利居民和激發城市活力,應該考慮逐步恢復和規范治理。他還以為發展地攤經濟不是臨時措施,而是值得常態發展。
姚洋說:“短期,我們有一個解決就業的目標,長期而言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我們的城市應變成什么樣的城市,是冷冰冰的城市,還是有溫度的城市。城市有了溫度之后才能解決就業,讓城市活起來。”姚洋指出,在發展和規范地攤經濟方面,地方領導干部應轉變觀念,并勇于承擔責任。
在疫情期間,由于防控需要,很多城市實際上已經默許乃至鼓勵臨街店展越門經營、大型商場占道促銷。疫情防控使餐飲業的堂食和商場的室內經營受到影響,室外展銷就成為企業復工復產的重要途徑之一。今年3月14日,成都市城市治理委員會、城市治理行政執法局印發《成都市城市治理五答應一堅持統籌疫情防控助力經濟發展措施》,更是為全國其他城市樹立了一個學習的榜樣。成都市政府堅持柔性執法和審慎包收留監管,答應地攤經濟在安全整潔的情況下恢復經營。成都市此舉看似是為了短期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權宜之計,實則具有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巨大潛力。
擺地攤在過往是很多城市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對于拉動靈活就業、激發創新活力、增加多源收進、便利居民生活、營造城市文化等都有較強的積極作用。但是,由于擺地攤而帶來的占道經營、無證經營、市場混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隱患和風險,使其一度成為各地政府爭相禁止的城市病。加之全國文明城市等城市品牌的創建都和擺地攤“過不往”,使地攤更是成為一些地方主政者的眼中釘肉中刺,可謂是不除不快。
在這種“圍追切斷”的政策態度下,城市治理職員和擺地攤的商戶之間經常上演貓和老鼠的游戲,城管與攤主的矛盾激化也每每釀成悲劇。如今我們只有在一些中小城市還能看到琳瑯滿目的地攤,在大城市已難覓擺地攤的蹤跡。城市一禁了之地全面清除了地攤,市收留環境的確大為改善,但是居民生活和城市活力卻受到極大影響。
地攤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業態,也是城市文化的一個側面。恰正是看似無序混亂的地攤才有熙來攘往的煙火氣,才成就了城市之為城市的繁榮與多元。城市究竟不能只有中心商務區,布滿生活氣味的地攤恰正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功能組團。舉凡令人記憶猶新和印象深刻的國際化大都市,都不乏帶有本地濃郁特色的各類地攤。以新加坡為例,在這座花園城市的大街小巷卻不乏小攤小販和熟食中心,為人們提供各色茶點和瓜果蔬菜,很多攤點都排著長長的隊伍,有些還是一座難求的明星店展。
地攤經濟也是一種地攤社會,提供各種機會并接納各色人等,體現出城市之為城市的多樣性和包收留性。果農和菜農進城零售瓜果蔬菜,既增加了他們的收進,也便利了市民的生活,并使低收進居民可以減少開支和改善生活。很多創業者的第一份工作和第一桶金,也往往是在擺攤練攤的過程中積累的。當地攤不再、活力失色時,城市就喪失了對底層社會的吸納和包收留,也抹殺了自下而上的社會活動渠道。
地攤銷聲匿跡,一些攤主為謀生路轉而進進門面房或開墻打洞,這讓地攤貨的價格低廉上風不再,也抬高了地攤創業就業的門檻。但是,對地攤經濟圍追切斷,不僅不會使其消失,反而可能節外生枝地制造新題目。比如,很多地攤由于城管執法而從地上轉進地下,從陽光下轉進陰影中,使灰色市場游離在法治之外,也使攤主和消費者都面臨違法經營和缺乏保障的風險。
關于一些城市對地攤因噎廢食和一禁了之的簡單粗暴做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多次給予痛批。在2016年4月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就指出,“我看到有些城市,街邊到處是小店,賣什么的都有,不僅群眾生活便利,整個城市也布滿活力。但有的城市規劃、治理觀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環境整潔’,犧牲了很多小商展。這樣的城市實在是一座毫無活力的‘死城’!”他談到,“之前有個別城市,夏天不讓農民拉西瓜的小板車進城,說是影響城市清潔,讓老百姓吃不上西瓜,農民也賺不到應有的收進。政府難道就沒有解決清潔題目的辦法嗎?”他進一步坦言,“說刺耳點,這不就是懶政嘛!”
之所以地攤會一直存在并令人期待,就在于市場需要和民眾呼喚,因此恢復地攤也是順應民意和回應民心。地攤經濟是城市治理能力的試金石,既可以檢驗城市治理者的執政理念是否與時俱進,也反映城市治理能力能否適應新情況和解決新題目。對此,李克強以為政府應進步城市規劃和治理能力,對地攤經濟不能光圖省事而一禁了之。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不僅應在疫情防控期間鼓勵城市恢復地攤經濟,而且還應將其作為一項可以長期堅持的發展方向。比如,目前很多城市大力發展夜間經濟,而地攤經濟恰正是夜間經濟發展的著力點,很難相信沒有地攤的城市夜晚可以發展出活力四射的夜間經濟。
首先,海運報價
國際快遞,應修訂涉及地攤經濟的上位法和規范性文件,不應對地攤經濟一禁了之,而應對其加以規范和扶持發展。比如,中心文明辦鑒于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形勢,明確要求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活動商販列為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和考核內收留,即是為各地政府恢復地攤經濟松了綁。當然,地攤經濟涉及城建、住房、交通、市場監管等多個領域的政府部分,需要加大力度清理分歧時宜的政策和制度,使地方政府可以無后顧之憂地發展地攤經濟。
其次,在一禁了之與放任自流之間,城市政府需要拿捏好度,做好地攤經濟的平衡術。要進一步提升城市精細化治理水平,平衡地攤經濟的各個方面,使其既有市場活力和消費動力,又能達到安全、健康、整潔等要求。比如,可以將網格化治理應用到地攤經濟的監管中,分片區、分業態和分時段地對地攤經濟進行分級分類治理,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地粗放式治理。
按經營時間來說,地攤有早市、夜市和季節性市場等。按經營場所來說,地攤既有另辟場地專門發展的,也有融進社區而大隱隱于市的。按經營品類來說,地攤有舊書攤、古玩市場,有理發、掏耳、修鞋等服務市場,也有菜市、水果攤、零食攤、燒烤攤等。就經營者來說,地攤有職業和兼職之分。加強對地攤經濟的分類規劃和精細化治理,將使地攤在規范發展的同時不添亂、不惹事。
最后,要創新對地攤經濟的監管,特別是用數字經濟和互聯網思維來進行治理。政府部分應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別是商事制度改革,對地攤經營者從簡從快辦理手續,使他們可以“最多跑一次”地完成登記注冊和申報事項,減少正當性本錢和審批門檻對地攤經濟的傷害。
同過往簡單粗放的地攤經濟相比,如今的地攤也實現“互聯網+”了。無論是賣菜還是賣瓜的路邊攤,隨處可見的是掃一掃的數字支付二維碼。借助于數字支付等互聯網技術,地攤千航國際經營的每個環節乃至每筆交易都處處留痕并有跡可循。地方政府恰恰需要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通過數字支付等渠道精準追蹤地攤經濟,并對地攤經濟加以規范發展。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 千航國際 |
| 國際空運 |
| 國際海運 |
| 國際快遞 |
| 跨境鐵路 |
| 多式聯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