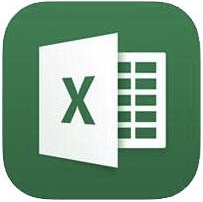為什么要為“地攤經濟”叫好?|李鐵談城市
?新聞 ????|???? ?2020-06-05 15:12
在制定城市政策的時候,要有換位思維,要多站在中等以下收進人口的角度往考慮題目:他們在城市要怎么樣生活,在生活和就業中會面臨哪些實際題目。
圖/視覺中國
2020年5月28日,西安,小南門里的夜市人氣火爆,食客在店外臨時支起的攤位上品嘗美食。
文 | 李鐵
近聞成都和西安市開始答應在城市的街道擺地攤,驚奇和贊許之中,似乎感到一陣東風撲面襲來,覺得有很多話想說。
近些年人們感受到了城市化的高速發展,城市面貌也發生了巨變。伴隨而來的是城市治理開始向發達國家的高標準看齊,試圖實現“水至清則無魚”的城市治理模式。
從各種所謂的治理“穿墻打洞”、清理低端人口、嚴格控制街區的視覺環境等,似乎是要使得我們的城市超越發達國家有著上百年發展歷史的城市,成為先進樣板。
在這種思維慣性下,我們的城市不僅在治理上更為挑剔和嚴格,可以說是“眼里收留不得沙子”,不答應與治理者主觀想象的景觀有任何偏差。在農村,曾經被各級政府招商引資來的大棚和農家樂被強制拆除,在城市,街頭商展被拆遷整治,公眾喜聞樂見的各種小門臉紛紛被清退,長期在城市里經營的個體攤點也被攆出城市,以換得城市居民的所謂安寧。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做法并不一定體現了生活在其中人們的心聲,更應該說是實現了個別治理者的“心靜”。
就業是人們最現實和緊迫的需求
當經濟和城市化高速增長的同時,人們經常被一些假象所迷惑。從城市景觀以及統計數字上,自已感覺已經開始步進了現代化,甚至超越了發達國家。至少在社會精英云集的超大城市和一些特大城市,似乎是有了這種盲目自大的感覺。也正是由于有了這種盲目自信,在城市治理上,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超越發展現實的各種要求,試圖要真正實現對發達國家的全面趕超,至少在城市面貌上要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對很多人來說,假如認真分析社會現實,還是能夠感受到與發達國家存在的巨大差距。這些差距并不只是所謂發展水平的題目,而是由于海量的人口,大大平攤了發展取得的成績。
例如,固然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了60%,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才44.38%,而且還有近40%的農村常住人口。一方面,中國面臨著如何提升城市化質量的艱巨任務,要把2億多在城鎮生活就業,卻難以與城鎮戶籍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務待遇的外來人口真正轉化為城市市民;另一方面,還要把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中轉移出來——按照城鎮化率70%的目標,還要轉移出1億多的農業人口。
這樣一來,各類城市相當于要接納4億左右的人口,并解決他們的就業穩定和安居題目。這些城市新增人口盡大部分都不是富人,而是中低收進者。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環境一定要和他們的收進水平相對吻合,他們需要的就業環境和生活空間同樣要與他們的收進水平相適應。
因此,在塑造城市的過程中,并不能忽視他們的這種消費和生活模式。要讓他們融進城市的生活,并且在有收進的基礎上,充分享受城市文明的熏陶,真正地實現市民化。當然,這需要漫長的時間,也許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或更長。
現實中還要面臨的另一個題目就是,城市人口將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據統計,中國中產階級人口加上高收進人口最多也就2.8億,而2018年,全國有效因私普通護照持有量僅1.3億本,意味著每年能夠因私出國旅游的人口只有1億多。假如算上有關方面統計的約4億中等收進群體人口,那就即是在中國總人口中,中等以上收進人口占比40%左右。
假定這些人都是城鎮常住人口,意味著在城鎮中還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中低收進人口。中低收進人口在城市生活面臨著比在農村更為嚴重的題目,首先就是城市的消費水平和物價遠遠高于農村。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人口多的大城市,生活消費水平和物價更是高于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
因此,在制定城市政策的時候,不能僅憑主觀臆測往考慮題目:城市應該怎么樣,未來怎么樣。而是要換位思維,要站在中等以下收進人口的角度往考慮題目:他們在城市要怎么樣生活,在生活和就業中會面臨哪些實際題目。
城市是解決生活和就業題目的最好空間。由于城市特點就是通過高密度的人口聚集來產生服務和就業需求,因此使得城市人口的收進水平可以穩步進步。
既然是創造就業和相互服務的空間,那怎么才能使城市的作用得到更好的發揮?
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兩類人的需求。對于中等以上收進人口制定的政策已經在逐步完善,而且從各類城市規劃和城市政策的文本上看,標準已經無比高大上。但是對于中等以下收進人口,似乎還有很大的欠缺,總是想能給他們點什么?例如,低保、舊房改造以及公共衛生環境的塑造。
城市治理者很少能考慮到,在一個高密度的城市空間里,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相互服務會產生什么樣的需求?這些人口的收進水平會支撐他們產生什么樣的消費,居住什么樣的住房,享受哪一類的公共服務等等。
正由于如此,大量城市政策忽視了中低收進人口最為現實和緊迫的需求,就是如何滿足他們在城市的就業,如何讓他們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獲得收進,而不是讓他們坐等低保和社會福利。
希看更多城市推廣新型地攤經濟
城市化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是,隨著城市發展,產業將逐漸退出中心城市,并向城市邊沿和遠郊區遷移,服務業在高密度的城市將取代產業的傳統地位。城市的出現源自于服務業,發展于產業,之后服務業又重新在城市占據主導地位,這是由城市發展規律所決定的。
服務業的特點是會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形成不同的就業形式。在城市發展初始階段,以貿易為主導的服務業是城市的主要產業。在城市化發展中期,服務業仍然離不開貿易,但是增加了金融業、科技業和地產業等新業態。到了城市現代化階段,信息革命、互聯網以及物聯網等新經濟形式固然促進服務業發生了本質變化。但無論哪個階段,貿易都牢牢地在城市占據著主導地位。原因在于,無論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人口結構和人的基本需求格式是亙古不變的。
在現實中,城市的人口階層存在著巨大的反差,跨境鐵路
國際物流,以傳統就業和生活方式生存的中低收進人口一直在城市存在,而且占有較大比重仍然是常態。而人的需求,固然與原始需求相比已經有了較大進步,但是對基本生活品和必須品的需求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假如承認這個現實,就需要根據人口的結構和基本需求,在適應現代化發展的同時來保持城市的基本特色,也就是既要提供科技、信息、互聯網等革命性需求所需要的空間載體,同時又要滿足中低收進人口最簡單的就業和生活需求。所謂“地攤”就是與這種需求直接相關的就業空間形式。
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政策說成為“接地氣”。實在就是接觸到中低收進人口的直接需求,而不是躺在各種“高大上”的夢幻中。長期以來,中心反復夸大以人為本,以人民為千航國際中心。實質就是在尊重城市發展階段的同時,更要尊重長期生活在社會最基層的城鄉居民。各類政策不能只滿足精英和富人的需求,而是要確保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些利益不是慈善的賜予,而是提供更多的機會和空間讓更多的人主動參與并分享發展的成果。
但在現實中,一些城市治理者往往憑借各種主觀思維模式就把這扇大門給封閉了。想一下,中低收進人口最需要的是價格便宜和生活方便,以及最為簡單的就業方式,而這其中就包括了快遞、外賣和街面經濟。假如在城市治理過程中,把服務內收留看得更多一點,將傳統就業方式的延續和以快遞為代表的新生“異象”,作為服務常態,并在服務中進行柔性治理,可能既會解決這些中低收進人口的收進題目,又會給所有居民提供更多的方便。
很多人以為,各種互聯網經營業態中的無人銷售和快遞模式,會產生對地攤經濟的替換。但是在大城市,漫長的上班路途,在重要的旅游景點,固定攤位有點像我們的公交站點,而地攤就像現在的共享單車,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要做的只是如何能夠滿足景觀和視覺以及公共衛生的需要。
在這方面政府可以大有作為。答應地攤存在的同時,可以提出相關要求,加強衛生監管,防止欺詐行為的發生。甚至,可以對地攤經營者進行業務培訓,并提供相對穩定的營業空間;還可以利用各種地攤模式形成城市的文化景觀。
總之,積極的改進方法很多,關鍵在于城市治理者的熟悉是否發生轉變。不僅是高層治理者和精英,而且更多的是基層治理者,甚至包括一部分自詡為城市精英的居民,他們能否做到“眼不見為凈”也是城市治理的難點。
可能會有很多人反對地攤,也反對中低收進人口所從事的就業崗位存在。他們的話語壟中斷權會直接影響到治理者的政策制定。正是由于如此,我們不僅希看成都和西安可以答應地攤經營形式的存在,而且更希看還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可以推廣地攤經營模式。當然,重要的是能否堅持,不能隨著某個領導的熟悉變化或者是某句話而任意取消。
城市治理能在充分尊重各種民意的同時,把身段放低一些,站在底層民眾的角度往考慮題目,這樣地攤經濟才可以持續。當然,答應不即是放任不管。把地攤作為支持中低收進居民就業的舉措之后,還可以塑造具有特色的城市景觀,千航國際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的實踐和探索。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 千航國際 |
| 國際空運 |
| 國際海運 |
| 國際快遞 |
| 跨境鐵路 |
| 多式聯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