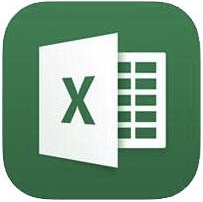美國的第五種權力:智庫
?物流新聞 ????|???? ?2020-06-04 16:41
1
智庫,英文“Think Tank”。
這個詞匯是二戰時期出現的,由美軍討論戰略和作戰計劃的保密室(Think Box)演變而來。
實質意義上的智庫有著悠久的歷史。戰國時期齊國的稷下學宮,已具備“資政、啟民、聚才、治學”等特點,可以已具智庫的雛形。
現代智庫的誕生,在美國。最早可溯源到19世紀初期的費城富蘭克林研究所,主要研究的是自然科學。
第一個專門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獨立智庫是1916年景立的政治研究所,也就是后來鼎鼎大名的布魯金斯學會。
2
有人說,美國事“小政府,大社會”。此評語正確與否,全看語境。
若是與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相比,確是如此。
可審閱美國自獨立以來的歷史,所謂的“小政府”,早已是18、19世紀的老黃歷了。
意識形態上,“自由”的價值觀依然最重要的。但在現實中,政府(包括國會)干預社會的權力擴大,才是美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先是不惜“違憲”之虞發動的南北戰爭,重塑了美國同一:重點在關稅和國內稅收的同一。若以死亡率看,南北戰爭甚至超過同時代的太平天國運動。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代價不可謂不高。
后來資本主義產業狂飆發展,誕生了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卡內基的美國鋼鐵公司、以及J.P.摩根等巨型托拉斯。激發了社會反托拉斯的運動,終極使得國會和政府把握了拆分企業的權力。
經濟的崛起,也使得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為自己的利益更加積極進取。制定適合的對外政策,理所當然成為政府的職責。
隨著聯邦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干預能力越來越強,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對于經濟信息的搜集以及政策的制定,卻遠遠落后于時代。
當時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與其說是出自社會科學,不如說是以官員及其背后利益團體為考量,在不同利益團體中交換妥協形成政策。例如,20世紀20年代的減稅政策,僅僅由于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自己是這個國家交稅第四多的公民,才熱衷于串聯國會議員(多是大富豪)推行減稅政策。
所以,在政治傳統和憲法的制約、本錢的考量下,政府內部又缺乏對經濟社會題目作出科學研究的專業機構,對外咨詢的需求就產生了。
當面臨逐漸強大的政府權力,“強社會”自然會產生影響或引導這樣的權力的想法,于是,資本家、企業家、學者、律師等整合了資源,供給也產生了。
在供需的協力下,促成現代智庫的誕生。
3
早期的智庫,明顯帶有“進步運動”時代的思潮痕跡。如布魯金斯學會的主旨是“為促進政府在各項活動中進步效率、厲行節約并進步科學水平而與政府官員合作,對政府工作進行科學研究的公民團體”。企圖影響政府政策和改革政府行為溢于言表。
要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是搜羅前任政府官員、商界高層、學者加進智庫;另一方面,智庫成為美國政治選舉中候選人籠絡的資源,進而為新上任的政府提供執政的思路和藍本。
例如布魯金斯學者勞林·亨利1959年出版《總統的轉型》,成為后來總統的“必讀書”。傳統基金會1980年推出《領導者的使命》成為里根政府職員的一本手冊。
因此,智庫與政府之間逐漸形成了“旋轉門”機制:智庫提供政策,新上任的總統為智庫的研究職員提供內閣的職位。任期結束后,這些有過政府工作經驗的人又回到智庫中。
美國智庫雖以“獨立性”為價值取向,但依然在意識形態、思想和政策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特別的政黨偏向。布魯金斯學會長期以來與民主黨合作,肯尼迪時期的“新邊疆”構想,林登·約翰遜時的“偉大社會”計劃方案都出自布魯金斯學會之手。奧巴馬執政時,32位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進進了他的執政團隊。因此有“民主黨流亡政府”、“民主黨思想庫”、“民主黨的影子內閣”之稱。
以“守舊主義智庫”著名的傳統基金會成立于1973年,由里根的“廚房內閣”的成員之一約瑟夫·庫爾斯和保羅·韋里奇創建。
1980年傳統基金會的學者推出《領導者的使命》一書,成為里根政府職員的一本手冊。2000年布什總統競選期間,傳統基金會為其提供醫療改革、教育、導彈防御等題目的政策,并出版的學術專著《一個成功總統的關鍵》。
近些年傳統基金會極力推廣“領導美國”的運動,把美國的“守舊主義”推動到新的階段。這個運動反對全民醫保制度,提出“讓每一個美國人都有選擇醫療保健的權利”;推崇自由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在維護美國的安全、自由和繁榮的條件下,解決能源與環境的題目——實際上是傾向石油利益團體,反對激進的環保主義,等等。
特朗普的“讓美國重新偉大”口號,就是從此運動的宗旨:“重塑開國元勛們最初的理想——讓美國變得富強”而來。
除了自由主義與守舊主義、共和黨與民主黨,軍工復合體,是隱躲在美國權力水面之下的龐然大物。
而大名鼎鼎的蘭德公司,則是吸收軍工復合體奶水長大的智庫。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軍方熟悉到有必要建立一個將軍事、科技、產業技術與信息結合在一起的研究機構。1945年,美國空軍與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簽署了一份共同進行“研究與開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計劃合同,其縮寫為RAND,即“蘭德計劃”。
該項目的主要任務是在軍方、政府情報部分、產業界和大學之間建立聯系,加強這些部分之間的合作和交流,并實現相互之間的資源共享。
1948年,在軍方的支持下,RAND從道格拉斯公司脫離出來,成為一家獨立和非營利性的研究機構。5月14日,蘭德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宗旨是:“通過促進、教育和慈善的發展,維護美國的公共福利和國家安全。”
此時的蘭德公司已經擁有超過200名不同領域的研究團隊,其成員包括數學家、物理學家、經濟學家、工程師、化學家、心理學家、空氣動力學家等方面的人才。
4
集金錢(基金會)、知識(學者專家)和政治影響力(前官員)于一身的智庫,其發展也越來越引起維護美國政治體制人士的擔心,他們想方想法“馴服”智庫。
所以在1969年美國國會通過稅務改革法,禁止基金會資助任何可能“影響”立法和政治競選結果的活動。
眾所周知,國際貨運
空運價格,私人基金會一直是智庫的主要資助人,這一時期,國會對智庫進行了極其嚴密的審查,還對智庫賴以獲得資助的很多基金會加以實實在在的限制。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基金會開始減少對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等智庫的資助。福特基金會一直是很多智庫的主要資金來源,在20世紀70-80年代開始減少了對智庫的資助。里根時期,政府完全取消了對住房的評估,使城市研究所的收進從80年代的1440萬美元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800萬美元。
這一趨勢,打破了私人基金會直接掌控智庫的局面,也就限制了智庫“政治團體化”。
智庫為了發展,不再畫地為牢。固然保持了其意識形態傾向,但智庫在努力擴展自己的客戶范圍,因而導致其所提供的政策咨詢更多考慮“公共性”,而非以執政黨或特定利益團體的態度為轉移。
例如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聯合編制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不僅是共和與民主黨政府制訂對內對外經濟政策時的重要參考,更是世界經濟學界具有指標性的報告。
而當輿論對于智庫的“公共性”產生質疑時,也會嚴重損害智庫的發展。如據英國《衛報》2007年2月的報道,美國企業研究所向有關科學家行賄,請他們批評聯合國政府間天氣變化專家小組的第四份評估報告。《衛報》另表露,企業研究所從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公司接受過160萬美元,而且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李·芮蒙德還是企業所理事會副主席。固然后來企業所澄清此事“子虛烏有”,但其聲譽還是受到一定損害,業務也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隨著8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多學科的長足進步,美國的政府規模增大、政策題目的復雜化和技術化、以及經濟的全球化,都促使了美國的智庫進進了一個快速發展階段。80年代新增的智庫數目,超過了1900年以來七十年景立的智庫數目的總和。
固然美國智庫以“非營利性組織”為名,但如此多的從業者,自然造成了更為激烈的同行競爭。
在這種環境下,要成為一個成功的智庫,就不應當只是“思考”(Think Tank),而更應當“思考轉化為實踐”(Think&Do Tank)、“傳播觀點”(Talk Tank)、“影響觀點”(Do Tank)以及“善用技術資源”(Techie Tank)。
于是美國智庫更注重自身的推廣和營銷,其的發展呈現業務多元化、規模化的特點。例如,原來依附軍方的蘭德公司,在80年代以后的研究范圍逐漸擴大到藝術、兒童政策、民事司法、教育、能源與環境、健康與保健、國際政策、國家安全、人口和老齡化、公眾安全、科學技術、藥物濫用、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交通和基礎設施、勞動力及其工作場所等領域。逐漸發展成為美國第一大智庫。
而智庫內部的運作,形成圍繞項目配置科研資源的模式:
在課題治理的程序上,重視課題進展中的監視,而且也很重視課題的評審。一般來說,課題研究的基本過程包括對相關題目進行事前調查、制訂調查研究計劃書、挑選合適職員組成課題研究小組、寫出中間報告、經過修改充實并寫出終極報告六個階段。對于每一項研究計劃,通常都有資深研究職員作評審員,負責計劃開始后的期中審查和計劃鄰近結束時的期末審查,以判定其是否達到了基金會設定的研究標準。
如在傳統基金會,每一位分析員寫出的報告,都必須先交本部分主任,提出修改意見;通過后,再交專業編輯進行文字方面的修改;最后交主管副會長過目。重要的研究報告需要交會長及總編輯過目。
5
美國智庫的發展路徑,有很深刻的美國政治體制與社會樣態的印記。
固然客戶也是以政府為主,但相比歐洲國家智庫多由政府或政黨直接成立,美國智庫的社會化和自主化的程度更高,智庫之間的競爭也更為激烈。
這種競爭機制,在政治性較小的政策或技術領域,會促使較高質量的聰明千航國際產品的出現。
但在近年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分裂情況愈加嚴重的環境下,一些著名智庫“公共性”減弱,“政治性”增強,非營利性和非政府性也更加模糊。
如今傳統基金會的經費主要來源于每年的召募捐款——20多萬的基金會成員、大企業公司、家族基金會和個人的捐助。以至于它的“守舊主義”色彩更加濃重,并被眾人視為守舊派的“忠實代理人”。
因此,原本被以為是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之后的“第五種權力”,充當學術界和決策團體,國家和社會公眾之間的橋梁,為服務公眾利益發出獨立的聲音的美國智庫,未來能否依然保持如此美譽,也是值得留意觀察的。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 千航國際 |
| 國際空運 |
| 國際海運 |
| 國際快遞 |
| 跨境鐵路 |
| 多式聯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