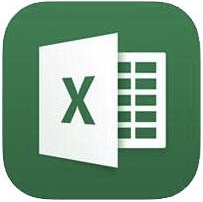看完《美國工廠》,歡迎來到“現實世界”
?物流新聞 ????|???? ?2020-06-04 16:42
文|李北辰
幾乎可以中斷言,《美國工廠》或許是2019年——甚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整個世界最重要的紀錄片。
經濟,政治,制度,文化,觀念,技術……不到兩小時的紀錄片,涵蓋了影響全球秩序的一切變量,這些變量相互交叉,賦予了《美國工廠》多重解釋角度。
而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某種理論和意識形態來熟悉世界的,你選擇從這部作品里看到什么,取決于你相信什么。
以下是我選擇相信的,我以為它更接近于現實。
1
先往返答一個題目:什么是“通過理論和意識形態”來熟悉世界?以及,人們該如何消弭這種偏見?
假如全世界只有一個人有資格回答這個題目,那么他一定就是弗朗西斯·福山。
伴隨著冷戰結束,福山在其1993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中表達了一個傲慢的觀點:自由民主制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終極形態。換句話說,現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
但此后十余年的歷史證實,制度本身的薄弱氣力,不足以穿透不同民族國家深厚的文化地層千航國際,人類正沿著多種多樣的現代化道路前進。作為一位老實的學者,現實與理念之間的鴻溝,也讓福山的題目意識慢慢轉向(“我的思想隨著歷史發展而發展”),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已開始將筆墨大幅傾向對所謂“國家建構”的論述。
什么是國家建構?
福山將其理解為政府的綜合治理能力。在他看來,國家政治分為三部分:法治,問責和國家建構。只有當三者達到平衡,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才有可能成為“現代政治的奇跡”,假如缺位或是“配比”不對,就會面臨一系列題目。
而這三者之間,“國家建構”最關鍵,是其他兩者的根基。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設施建設的迂緩,歐洲高福利國家的滯漲,乃至美國赤字題目,都是國家建構能力缺失的體現。
再具體點說,譬如在福山看來,美國政治衰敗的一個表象,就是利益團體可以正當地影響當政精英。
而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工廠》這部紀錄片,恰正是窺探上述理論的一面鏡子:在整個故事里,資本家,普通工人,利益團體,“反工會”的公司,各方皆為私利博弈,這無可厚非,但你似乎就是找不到最重要的“國家建構”那部分。
2
逐一拆解的話,在《美國工廠》里,來自大洋彼岸的福耀,有著一顆最單純的心:賺錢。
實在當年福耀決定往美國建廠,輿論的一片喧嘩,本身就已折射出什么是“透過理論和意識形態”來熟悉世界。
當年作為中國制造業外遷的“樣本”(實在并不具有代表性),媒體熱衷于解讀其赴美動機,甚至上升為“曹德旺要跑了”的高度。但現實中,福耀往美國設廠的最大原因就是玻璃運輸講究親疏遠近,要靠近當地的客戶,美國大型汽車制造商每年都會購買數以百萬計的擋風玻璃。
事實上,在談論中國制造業外遷時,就像學者發揮所言:那種對供給鏈要求不高,且對于遠間隔物流本錢較為敏感的制造業,就能轉走。“一種產品對物流本錢是否敏感,有個很簡單的判定標準,就是單位重量的產品售價。假如售價比較高,就不敏感,比如手機;假如售價比較低就敏感,比如玻璃、低標號水泥、粗陶瓷之類的。像玻璃、水泥這樣的產品適合就近生產,不適合在間隔銷售市場很遠的地方生產,這樣物流本錢太高,不劃算。所以這樣的產業能夠被轉走,也應該轉移走,這符合經濟規律。”
福耀在美國建廠當然符合經濟規律,曹德旺還給美國市場設定了2017年盈利2億美元的目標。
但這卻讓美國工人怨聲載道。
相比于世間所有的“大道理”,工人的訴求倒是接近于普世:錢多,活少。于是在短暫的蜜月期后,他們開始抱怨任務重,環境熱,安全沒保障,并開始涌上街頭,謀劃在福耀工廠成立工會。
實在早在工廠竣工慶典當天,州議員Sherrod Brown就分歧時宜地談及“俄亥俄州有著悠久的工會歷史”。
但博弈的另一邊,正如曹德旺所言:“我們不愿意看到工會在這里發展,由于工會影響勞動效率,直接造成損失。工會進來,我關門不做了。”
要知道,在自由論者的“理論框架”中,工會快成了阻礙美國經濟發展的蛀蟲,但我并不懷疑工會制約氣力的的初衷,真正的題目是,工會在美國已演變為分工專業,技術嫻熟的利益團體——事實上,相比于輪流坐莊制,如今美國政治的本質,更像是利益團體博弈制,無論任何組織,海運費,只要影響力足夠大,就能與政府討價還價,還可游說國會議員通過對其有利的立法。
譬如,《美國工廠》里成立于1936年的UAW(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就專注于為汽車工人謀取高福利,它曾讓福特,通用,克萊斯勒等汽車巨頭集體膽冷。
在部分經濟學者眼中,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間接造成了底特律的破產,紀錄片里也一度讓福耀疲憊不堪。
但戲還沒完,還有反轉。
你當然可以說是哈耶克“自發擴展秩序”的某種體現,當環境中出現工會這個物種,生態位的另一端就會自發演化出LRI 這種反工會組織,有著“工會克星”之稱的LRI同樣洞悉工人階級的心理,通過各種權謀將工會打敗,福耀僅僅是向LRI正當支付了100萬美金。
至此,各方利益博弈暫告段落。
但我不知你發現了什么沒有?事實上,就像學者李子旸指出的那樣,在整個博弈過程里,“福耀是投資者,想的是利潤。工人是勞動者,想的是少干活多拿錢工作輕松。工會是利益團體,想的是擴大影響力增加會員。幫著福耀搞定工會的LRI 是公司,想的是把這個項目做好,多賺錢。誰負責美國的整體利益呢?誰負責代頓這個社區的利益呢?這個角色一直缺席,可能根本就沒有。”
有人說特朗普正在彌補這個角色,或許吧。
3
至少在一部分人眼中,某種程度上,正是國家建構的缺失,讓美國中低層藍領階級,并未從全球化中受益。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曾提出“全球化的政治三難選擇”,在羅德里克看來,一個國家可以選擇“世界經濟一體化”,“民族國家”和“大眾政治”三個目標,但你不能全要,只能三選二。
這是由于,自由貿易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通過分工讓本國經濟利益“最大化”,卻不可能通過“自發擴展秩序”讓本國所有人都滿足,它終會帶來贏家和輸家,以及二者的潛伏摩擦。
“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程度受到其碰到的外部沖擊和國內治理能力的影響。外部沖擊越大,對外開放就越要謹慎,國內治理能力越強,能夠實現的對外開放程度就越高”,誠如經濟學者何帆所言:“我們不能像特朗普那樣修一堵墻,把千航國際自己和外部的世界隔盡,但也不能毫無防守,最好的辦法是在墻上開一個門。門是敞開的,但要保存在危機時期關上大門的實力。”
我不知道對于中美兩國來說,這道“門”現在屬于開著還是關著。假如是關著的,那么《美國工廠》這部紀錄片,就有點像是這道門上的門鏡,它可以讓各自分別窺探到對方的存在,并進一步理解對方。
令人動收留的是,在片中某些非理性的瞬間,甚至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在福耀中國工廠的晚會上,面對中國小女孩的集體表演,和幾對中國新人的集體婚禮,一位遠道而來的福耀美國高管,面對鏡頭流下了一種只可能出現在異域風情的感動淚水,“我感到,我們是一個……巨大的星球。一個有些分裂的世界……但我們仍然是一體的。”
但遺憾的是,現實恰恰與之相反,這部《美國工廠》讓人們知道:人類沒有大同,差異沒有泯滅。
在真實世界,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航船,你我每個人都在甲板上,隨著它乘風破浪,搖搖擺晃。
作者:李北辰,獨立撰稿人,國內數十家媒體專欄作家,曾供職《南都周刊》《華夏時報》《財經》等媒體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國際物流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 千航國際 |
| 國際空運 |
| 國際海運 |
| 國際快遞 |
| 跨境鐵路 |
| 多式聯運 |